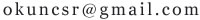《地久天长》|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
来源:编辑vide
说到极致了的话,是“最”,是“一定”,是“唯一”,是“没有你我会死”,是“一辈子”,是“永远”……
还有这决绝的电影名字《地久天长》,天是很长,地也好久。可终究会有幻灭的一天,虽然那时我早已归为尘土。
还是觉得英文名字“So long,my son”更为朴实动人,如此漫长,我的孩子。观影时,《地久天长》这个名字我没有动心,看到旁边飘过的英文字幕:So long,my son,不禁热泪盈眶。
是的,我不能失去你,我的孩子。只在看到英文名字的这一时刻,被感动到了。接着是漫长的173分钟,坐在宽大幽暗的影院里,观赏这部在德国获了双帝奖的影片《地久天长》。
电影讲述的是80年代初及以后的三十年间,在时代的变迁里,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。耀军丽云一家,和同事英明、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,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,同年同月同日生,双方父母约定定“一辈子做兄弟”。然而,英明的妻子海燕因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所在,逼迫丽云打掉二胎,导致大出血而一生不育。
几年后,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,耀军痛失独子刘星。从此,孩子永逝的阴影侵袭着耀军和丽云的身心,他们辗转南下,经营着一家修车铺,名字为“星星修车行”。
多年以后,海燕患癌,惦念耀军和丽云,邀请他俩回来,一群人又聚在一起,庆祝沈浩孩子的出生,其乐融融,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
记得没看电影之前,就看到一些评论说,“克制隐忍”之类的词,观影之后,只想问,哪个时代,芸芸众生里个体的命运里,不都是如此挣扎着,“隐忍”,“克制”,以为这是成年人混社会的必须品质。
浩大的时代里,几家人的心酸。于更广阔的天地里去看,世世代代,无有分别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烙印。即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“共业”,去承担忍受,佛家讲“果受”。其实不需要放大赞美,刻意渲染,即使是在相对自由表达的时代。
……独生子女。空巢老人。留守儿童。下岗。下海经商。出国。待业。二胎。医疗。住房。教育。婚姻。爱情。……
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世的悲剧。天生万物,上苍要带走谁,不会跟他身边的人商量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与困惑,此消彼长,看似失衡不公,实则万物自有其守恒定律。
《延禧攻略》那样的抗争怨怼的爽剧,并不是现实生活里大多数人可以复制模仿的样本。
至于说男主女主的表演,不是国外获个奖就怎样了。个人以为和陈道明和巩俐的《归来》不可同日而语,甚至也远不如刘敏涛和陈创在电视剧《富贵》里的表演(改编自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)。
在触动心弦和戳人眼泪的点上,甚至都不能和电影《芳华》并论,何小萍穿着病号服在草地上独舞那一段极戳泪点。溶溶夜色,没有舞台,灯光,配乐,但一切美得让人掉泪。片尾,小萍依靠在刘峰的肩头,孤单落寞的两人,温暖依偎,令观者唏嘘。
电影《亲爱的》里有“找孩子”组织,失孤的父母报团互助,有的找到了,更多的还是无尽的的等待。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,才是最撕扯人心的事吧。现实比电影冷酷,父母在心里终生寻找自己的孩子,被渺茫的希望煎熬着,身体却不得不在正常的生活轨迹里辗转流离。
终生寻找,或者无力承受去寻死,都是现实里极端的个例。
山河满目,独缺你一个。大抵,是人间悲催至极吧。尤其在这个春光明媚的季节,看着满地的落花纷飞,念什么天长地久,兔走乌飞。
《天长地久》看完,只觉得创作者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最懂得“克制隐忍”的人,他以他的方式表达出来,只是没有走近很多观众的内心。
我不是创作者,作为买单的观众,不能触动内心的,便不是我名单里的好片,且不值得再看。
如果说《地久天长》要表达传递什么,主题音乐《友谊天长地久》似乎才是很好的暗示吧。
最初这是一首非常出名的诗歌,原文是逝去已久的日子。后来被谱了乐曲,被很多国家传唱,在亚洲地区中的毕业礼或葬礼中常被选为主题曲,象征着一段告别或结束的情感。
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《友谊地久天长》这段旋律,应该是来自《魂断蓝桥》,一部风靡世界近半个世纪的黑白电影,是战争时期催人泪下的爱情绝唱。
明明是个悲伤的死别故事,魂断梦碎,偏要在一段音乐里诉说着一路平安,祝愿着天长地久。
《地久天长》里,风华少年王源娓娓道来的歌声,温柔动人,却有一种克制的悲伤。观影时,每当这段旋律响起,就会有短暂的百感交集。
“怎能忘记旧日朋友,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,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。
我们曾经终日游荡,在故乡的青山上,我们也曾历尽苦辛,到处奔波流浪。……
我们往日情意相投,让我们紧握双手,来举杯畅饮,友谊地久天长。”
时代洪流中,激发了人性的恶,也闪耀着人性的善。漫长的岁月里,其实两家一直怀念曾经的友情,最终选择原谅和解,在有生之年放下过去微笑向前。
如果这样理解,或许可以明了《地久天长》欲呈现的主题,离别珍重友谊永存。至于放在时代浪潮里去表达,则有些牵强无力。
看完这部电影后的一天,在电梯里看到一张《地久天长》的海报底端赫然四个字“春暖人心”,而看完却有一种莫名的愁绪,只觉“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”。
想起电影里两句很文艺的话,在剧中听起来十分地不合时宜,有观众在笑,我也感觉莫名其妙。
耀军说:“用她(丽云)的话来说,时间已经停止了,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。”
丽云说:“都这样了,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面对的呢?”
成年的沈浩一大段极度非口语的台词:“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,我在长大,大树也在长大,我感觉自己要被撑破了……(大意如此)”
小时候沈浩知道是自己在河里推了刘星一把,导致刘星身亡。很多年过去了,没人去谈论这个话题,沈浩的告白请求原谅,丽云选择原谅:“孩子,说出来就好了。”
整个观影过程中,这三段话听起来有些许怪异,大实话是和剧中人物身份不搭调。这三段对话如果剪辑了,也并不会影响这部电影的主题呈现。而回头再次想起这几段情节,觉得无比地荒诞与悲凉,或许这就是真实的人间吧。
电影始终是电影,美化着感同身受的负疚感,和貌似放下过去的平静洒脱。荒草丛生的墓碑前,可以若无其事地想念未成年的独子么。如此漫长的一生,我的孩子,可是你早已不在。或许这才是白发人的心声吧。
我无法确定,只是每当生死离别的时刻,总想起顾城的一首短诗《墓床》:
“我知道永逝降临,并不悲伤,
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,
下边有海,远看像水池,
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,
人时已尽,人世很长,
我在中间应当休息,
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,
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。”
有很浅的意像,很深的意境,凝重而超然。最初读这首诗,内心是脆弱的,后来是坚强的,再后来是悲悯的,为着逝去,为着不能拥有,为着唯一,也为着无法言说的过往,和不可期许的未来,还有每时每刻的幻灭。
有次,女儿放学回来,叹了口气说,妈妈,今天老师给我们看了《人间世》,我们同学都表示庆幸,自己毫发未伤地这么大真是不容易呀。
当时我一怔,只简单地回应了一句,可不是嘛。
这次看了《地久天长》,我问妈妈,那个时候真的这样逼人打胎吗?妈妈说,可不是嘛,记得认识的一个姐妹,都六个多月了,也被迫去做了引产,是个男孩,真是造孽呀。
那他们为什么不逃走呢?我总是这样问。能往哪里逃呢,也就是演电影吧,妈妈说。
我竟有点儿心有余悸,跟女儿一个感受,毫发未损地活这么大,真不容易。个体是沧海一粟,我就是那粒微尘。
不过,我始终知道,在父母眼里,我是他们的命,在孩子眼里,我是她的天。
我喜欢春天的桃花,夏天海的浪花,秋天的银杏叶,和冬天的雪花,和每天的你。 可如果没有了你,过眼的风景都会黯然失色,不值留恋,我的宝贝。
我是他们的唯一。我有广阔的天地,他们就有。以前总是豪言壮语,为了什么而奋斗,对各种关系没有排序。现在依然有豪情在心底,不过会郑重地把身边的他们放在第一位。
天是否长,地是否久,永远有多远,和我有什么关系。天长地久太远了,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,我不要。漫漫人生路,我只要和你在一起,我的孩子,我的亲朋好友,愿无事常相见。
~
还有这决绝的电影名字《地久天长》,天是很长,地也好久。可终究会有幻灭的一天,虽然那时我早已归为尘土。
还是觉得英文名字“So long,my son”更为朴实动人,如此漫长,我的孩子。观影时,《地久天长》这个名字我没有动心,看到旁边飘过的英文字幕:So long,my son,不禁热泪盈眶。
是的,我不能失去你,我的孩子。只在看到英文名字的这一时刻,被感动到了。接着是漫长的173分钟,坐在宽大幽暗的影院里,观赏这部在德国获了双帝奖的影片《地久天长》。
电影讲述的是80年代初及以后的三十年间,在时代的变迁里,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。耀军丽云一家,和同事英明、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,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,同年同月同日生,双方父母约定定“一辈子做兄弟”。然而,英明的妻子海燕因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所在,逼迫丽云打掉二胎,导致大出血而一生不育。
几年后,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,耀军痛失独子刘星。从此,孩子永逝的阴影侵袭着耀军和丽云的身心,他们辗转南下,经营着一家修车铺,名字为“星星修车行”。
多年以后,海燕患癌,惦念耀军和丽云,邀请他俩回来,一群人又聚在一起,庆祝沈浩孩子的出生,其乐融融,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
记得没看电影之前,就看到一些评论说,“克制隐忍”之类的词,观影之后,只想问,哪个时代,芸芸众生里个体的命运里,不都是如此挣扎着,“隐忍”,“克制”,以为这是成年人混社会的必须品质。
浩大的时代里,几家人的心酸。于更广阔的天地里去看,世世代代,无有分别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烙印。即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“共业”,去承担忍受,佛家讲“果受”。其实不需要放大赞美,刻意渲染,即使是在相对自由表达的时代。
……独生子女。空巢老人。留守儿童。下岗。下海经商。出国。待业。二胎。医疗。住房。教育。婚姻。爱情。……
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世的悲剧。天生万物,上苍要带走谁,不会跟他身边的人商量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与困惑,此消彼长,看似失衡不公,实则万物自有其守恒定律。
《延禧攻略》那样的抗争怨怼的爽剧,并不是现实生活里大多数人可以复制模仿的样本。
至于说男主女主的表演,不是国外获个奖就怎样了。个人以为和陈道明和巩俐的《归来》不可同日而语,甚至也远不如刘敏涛和陈创在电视剧《富贵》里的表演(改编自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)。
在触动心弦和戳人眼泪的点上,甚至都不能和电影《芳华》并论,何小萍穿着病号服在草地上独舞那一段极戳泪点。溶溶夜色,没有舞台,灯光,配乐,但一切美得让人掉泪。片尾,小萍依靠在刘峰的肩头,孤单落寞的两人,温暖依偎,令观者唏嘘。
电影《亲爱的》里有“找孩子”组织,失孤的父母报团互助,有的找到了,更多的还是无尽的的等待。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,才是最撕扯人心的事吧。现实比电影冷酷,父母在心里终生寻找自己的孩子,被渺茫的希望煎熬着,身体却不得不在正常的生活轨迹里辗转流离。
终生寻找,或者无力承受去寻死,都是现实里极端的个例。
山河满目,独缺你一个。大抵,是人间悲催至极吧。尤其在这个春光明媚的季节,看着满地的落花纷飞,念什么天长地久,兔走乌飞。
《天长地久》看完,只觉得创作者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最懂得“克制隐忍”的人,他以他的方式表达出来,只是没有走近很多观众的内心。
我不是创作者,作为买单的观众,不能触动内心的,便不是我名单里的好片,且不值得再看。
如果说《地久天长》要表达传递什么,主题音乐《友谊天长地久》似乎才是很好的暗示吧。
最初这是一首非常出名的诗歌,原文是逝去已久的日子。后来被谱了乐曲,被很多国家传唱,在亚洲地区中的毕业礼或葬礼中常被选为主题曲,象征着一段告别或结束的情感。
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《友谊地久天长》这段旋律,应该是来自《魂断蓝桥》,一部风靡世界近半个世纪的黑白电影,是战争时期催人泪下的爱情绝唱。
明明是个悲伤的死别故事,魂断梦碎,偏要在一段音乐里诉说着一路平安,祝愿着天长地久。
《地久天长》里,风华少年王源娓娓道来的歌声,温柔动人,却有一种克制的悲伤。观影时,每当这段旋律响起,就会有短暂的百感交集。
“怎能忘记旧日朋友,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,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。
我们曾经终日游荡,在故乡的青山上,我们也曾历尽苦辛,到处奔波流浪。……
我们往日情意相投,让我们紧握双手,来举杯畅饮,友谊地久天长。”
时代洪流中,激发了人性的恶,也闪耀着人性的善。漫长的岁月里,其实两家一直怀念曾经的友情,最终选择原谅和解,在有生之年放下过去微笑向前。
如果这样理解,或许可以明了《地久天长》欲呈现的主题,离别珍重友谊永存。至于放在时代浪潮里去表达,则有些牵强无力。
看完这部电影后的一天,在电梯里看到一张《地久天长》的海报底端赫然四个字“春暖人心”,而看完却有一种莫名的愁绪,只觉“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”。
想起电影里两句很文艺的话,在剧中听起来十分地不合时宜,有观众在笑,我也感觉莫名其妙。
耀军说:“用她(丽云)的话来说,时间已经停止了,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。”
丽云说:“都这样了,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面对的呢?”
成年的沈浩一大段极度非口语的台词:“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,我在长大,大树也在长大,我感觉自己要被撑破了……(大意如此)”
小时候沈浩知道是自己在河里推了刘星一把,导致刘星身亡。很多年过去了,没人去谈论这个话题,沈浩的告白请求原谅,丽云选择原谅:“孩子,说出来就好了。”
整个观影过程中,这三段话听起来有些许怪异,大实话是和剧中人物身份不搭调。这三段对话如果剪辑了,也并不会影响这部电影的主题呈现。而回头再次想起这几段情节,觉得无比地荒诞与悲凉,或许这就是真实的人间吧。
电影始终是电影,美化着感同身受的负疚感,和貌似放下过去的平静洒脱。荒草丛生的墓碑前,可以若无其事地想念未成年的独子么。如此漫长的一生,我的孩子,可是你早已不在。或许这才是白发人的心声吧。
我无法确定,只是每当生死离别的时刻,总想起顾城的一首短诗《墓床》:
“我知道永逝降临,并不悲伤,
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,
下边有海,远看像水池,
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,
人时已尽,人世很长,
我在中间应当休息,
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,
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。”
有很浅的意像,很深的意境,凝重而超然。最初读这首诗,内心是脆弱的,后来是坚强的,再后来是悲悯的,为着逝去,为着不能拥有,为着唯一,也为着无法言说的过往,和不可期许的未来,还有每时每刻的幻灭。
有次,女儿放学回来,叹了口气说,妈妈,今天老师给我们看了《人间世》,我们同学都表示庆幸,自己毫发未伤地这么大真是不容易呀。
当时我一怔,只简单地回应了一句,可不是嘛。
这次看了《地久天长》,我问妈妈,那个时候真的这样逼人打胎吗?妈妈说,可不是嘛,记得认识的一个姐妹,都六个多月了,也被迫去做了引产,是个男孩,真是造孽呀。
那他们为什么不逃走呢?我总是这样问。能往哪里逃呢,也就是演电影吧,妈妈说。
我竟有点儿心有余悸,跟女儿一个感受,毫发未损地活这么大,真不容易。个体是沧海一粟,我就是那粒微尘。
不过,我始终知道,在父母眼里,我是他们的命,在孩子眼里,我是她的天。
我喜欢春天的桃花,夏天海的浪花,秋天的银杏叶,和冬天的雪花,和每天的你。 可如果没有了你,过眼的风景都会黯然失色,不值留恋,我的宝贝。
我是他们的唯一。我有广阔的天地,他们就有。以前总是豪言壮语,为了什么而奋斗,对各种关系没有排序。现在依然有豪情在心底,不过会郑重地把身边的他们放在第一位。
天是否长,地是否久,永远有多远,和我有什么关系。天长地久太远了,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,我不要。漫漫人生路,我只要和你在一起,我的孩子,我的亲朋好友,愿无事常相见。
~